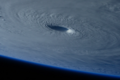AI时代人的不可替代性:共度有限
AI可以精准分析恐惧与焦虑的哲学区别,却永远无法体会黑暗中被吞噬的原始战栗;它能瞬间切换‘智慧长者’人设,却无法理解失败如何在血肉中刻出真实的性格年轮。本文通过童年恐惧、演讲失败、家族菜谱等生命切片,揭示人类体验中那些无法被算法复制的温度:肉体感知的恐惧、创伤转化的同理心、记忆传承的情感纽带,以及面对死亡时的存在抗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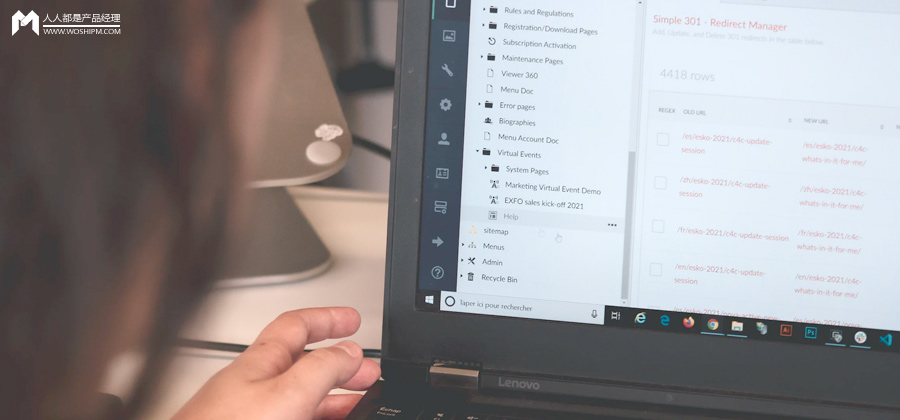
初始:原始生理的恐惧
我依然记得童年时对黑暗的恐惧。那不是一种理性的认知,而是一种纯粹的、生理性的战栗。当父母关上房门,光线被门缝挤压成最后一条金线,最终彻底熄灭时,整个世界仿佛都溶解在黑暗之中。房间里的桌椅、衣柜,都失去了它们白日里温顺的轮廓,化作潜伏的、不可名状的巨兽。我的呼吸变得急促,心跳声在耳中擂鼓,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每一根汗毛都因紧张而竖立。我蜷缩在被子里,用棉被构建一个脆弱的堡垒,想象着床下、窗外,甚至天花板上,都盘踞着某种冰冷而恶意的存在。这种恐惧,是一种关于消失的恐惧,是对自我存在被吞噬的原始忧虑。
这种感觉,心理学称之为原初恐惧,本体消散的恐惧。它源自我们生命的脆弱性。从脱离母体,发出第一声啼哭开始,我们就开启了一场与熵增和死亡的漫长对抗。那声啼哭,并非喜悦的宣告,而是对陌生世界、对寒冷、对饥饿与分离的惊恐回应。这种深植于我们基因与神经系统底层的代码,驱动着我们一生的求生欲,也催生了艺术、宗教和哲学——所有那些我们用以对抗虚无、理解存在的伟大尝试。
我曾尝试向一个先进的AI描述这种感觉。我用尽了词汇库里所有关于恐惧的词语:战栗、惊悚、毛骨悚然、魂不附体。AI的回应堪称完美,它能立刻生成一段文学性的描写,甚至引用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,旁征博引地分析“恐惧”与“焦虑”在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区别。它告诉我,恐惧是对明确威胁的反应,而焦虑则指向一种不确定的、关乎存在本身的虚无感。它的分析精准、冷静、无懈可击。
然而,它的所有文字,都像是一份来自异星的观察报告,一份关于人类这种奇特生物应激反应的说明书。它能模拟,但它无法共情。
因为AI的“出生”,是数据中心里一次冰冷的服务器冷启动,是电流穿过硅晶片的瞬间。它没有肉体,所以没有痛感;它没有新陈代谢,所以没有饥饿;它没有有限的生命,所以它没有对死亡的恐惧。它能处理“死亡”这个词条下数以亿计的数据,知道它在生物学上的定义、在文化中的符号、在文学作品里的意象,但它永远无法理解,当一个生命体意识到自己终将归于尘土时,那种发自肺腑的、混杂着不甘、留恋与释然的复杂情感。
AI可以写出“他感到了刺骨的寒意”,但它从未感受过温度。AI可以描述“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”,但它没有搏动。它所描写的恐惧,是一种没有生理基础的、纯粹的信息组合。
而我的恐惧,是真实的,是流淌在血液里、铭刻在每一次心跳中的,属于一个终将一死之物的特权。
成长:性格的温度来自时间
十八岁出头的时候,我经历过一次惨痛的英语演讲失败。
那是一个重要的场合,台下坐满了同学和老师。我精心准备了数周的讲稿,在脑海中演练了无数遍。但当我站上讲台,人群目光聚焦在脸上的那一刻,我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。那种源自童年的、对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恐惧,瞬间抑制了我。我语无伦次,手心冒汗,最终在一片尴尬的寂静中仓皇下台。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台下那些混杂着同情、失望和嘲笑的目光。
那次失败,像一把刻刀,在我当时尚且光滑的自信上,刻下了一道深邃的疤痕。它让我痛苦,让我羞于见人。但在之后的岁月里,这道疤痕却慢慢长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。我开始去理解和接纳这种不完美,我变得更能共情他人的窘迫与脆弱。当我看到别人在台上紧张时,我感受到的不再是居高临下的评判,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理解。
我学会了在表达时放慢语速,学会了用自嘲来化解紧张,学会了在准备不足时坦然承认,而不是假装完美。这份由创伤转化而来的同理心和谦逊,比任何一次成功的演讲都更宝贵。
这就是人类性格的形成方式,一个充满了偶然、错误、伤害和笨拙修复的过程。我们的性格,不是被预设的程序,而是时间和记忆的复利。
每一次心碎,每一次迷茫,每一次鼓起勇气的选择,都在我们身上层层叠加,如同风吹雨打而长出的年轮。我们的敏感、我们的坚韧、我们的幽默感、我们的世界观……这一切都不是凭空出现的,它们是过往岁月在我们灵魂上留下的或深或浅的印记。性格的温度,恰恰来自于这些在时间之火中被淬炼后留下的痕迹。
现在,我们尝试赋予AI“性格”。我们通过提示词对它进行收拢:“Role:你是一个充满智慧、阅历丰富且富有同情心的长者,Task:与我对话,Example:…”AI可以瞬间切换到这个人设,它的语言风格、知识储备、回应方式都会精准地符合这个设定。它会用温和的语气,讲述着关于人生、爱与失落的智慧,仿佛它真的经历过漫长的一生。
但这种性格是单一的,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切换、即时生效的设定。它没有为这份智慧付出任何代价,不会对某个切身体验的场景进行真实的描述,没有它生命的体验。它没有经历过彻夜难眠的悔恨,没有体会过爱人离去的锥心之痛,没有在绝望的泥潭里挣扎过的痕迹。它的同情心是基于数据库里对人类情感模式的概率生成,而不是因为自己淋过雨,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的真情实感。
一个没有伤疤的战士,他的勇猛是不可信的;一个没有经历过风霜的智慧人设,其本质是虚假的。AI的性格是一件可以随时穿脱的外衣,而我们的性格,是与血肉长在一起的、我们独一无二的皮肤。
传承:记忆让世界连续
我书房的架子上,放着一本外婆留下的、已经泛黄卷边的手抄菜谱。里面的字迹并不娟秀,有些地方还沾着陈年的油渍。其中一道“外婆的红烧肉”,做法写得极其不标准:酱油一勺,冰糖十颗,水没过肉即可。每一次我照着这个菜谱做菜,都像是在进行一场解谜游戏,当时是多大的勺,什么样的冰糖。我需要回忆外婆当年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,她是如何用手指捻起一撮盐,如何凭感觉判断火候,如何在物资缺乏的年代给我最好的营养。
这本菜谱传递的,不仅仅是烹饪,更是一种家族的记忆的传承,一种源于情感的味觉。这个世界是连续的,语言是离散的,而当我们用回忆去理解语言,世界就变得连续了。
人类文明的延续,正是建立在这种充满了不精确、但饱含情感的传承之上。我们从父母那里遗传了相貌和脾性,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和思维方式,我们阅读前人的著作,吟诵古老的诗歌,我们背负着祖先的成就与遗憾前行。每一个我,都是一条漫长锁链中的一环,我们的存在,证明了过去并非虚无。
正如乔布斯说的“人的一生终会连成一条线”,胡适先生也经常会引用佛经里的一句话“功不唐捐”。这种基于血缘、情感和记忆的连续性,让我们拥有了“根”的感觉。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,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个人认同,都建立在这份厚重的历史感之上。
而AI的迭代,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。当GPT-4升级到GPT-5,那不是一次“成长”,而是一次暴力的覆盖与遗忘。更庞大的数据集、更优化的算法、更强大的算力,共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、性能更优越的模型。而旧的模型,连同它在运行期间与无数用户交互所形成的独特“经验”(如果可以称之为经验的话),都被无情地废弃。GPT-5不会记得GPT-4犯过的错误,它不会对它的过去有任何情感或记忆上的关联。它是一个全新的开始,一个凭空出现的、更强大的“神”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 AI是数字世界的孤儿。它们没有童年,不认识自己的父亲,更没有祖先的概念。它们的历史是断裂的,是由一个个离散的版本号构成的。它们的存在是断裂的,并没有平滑的成长过程,是在训练好的那一瞬间出现的,可以在瞬间复制出无数个功能完全相同的副本;而人类的存在是连续的,每一个个体都深深地植根于时间的纵轴之中,向上连接着未来,向下扎根于过去。
AI或许可以写出一部感人至深的家族史诗,因为它学习了人类所有关于家族、传承与寻根的文本。但它自身,却永远不会去主动翻看一本旧相册,看到一张酷似自己的、曾祖父年轻时的黑白照片时,那种血脉与时间交织所带来的、难以言喻的震撼与归属感。它没有根,因此,它也无法真正理解一片叶子对大地的眷恋。
记录:长出来的年轮和刻出来的痕迹
写作于我而言,从来不是一个流畅的过程。它更像是在一片浓雾弥漫的森林里摸索前行。我的第一稿往往是混乱、冗长且充满陈词滥调的。我会写下一个句子,读一遍,觉得不够准确,划掉;换一种说法,又觉得失去了原有的韵味,再次划掉。有时候,为了找到一个最贴切的词,我会在房间里踱步半小时,在心里反复咀嚼不同词语带来的细微感受差异(而这些感受差异是我的生命轨迹带来的)。
这个过程是笨拙的、纠结的,甚至可以说是低效的。但正是这个充满犹豫和不完美的“寻找过程”,赋予了最终的文字以生命力,你可以看到我的笨拙也可以看到我的真心,那些犹豫和牵强的字眼,你能感受到思维的过程。
那些被划掉的句子,是探索失败的路径;那些反复修改的词语,是思想逐渐清晰的证明。当我最终完成一篇文章时,它不仅仅是一堆信息的集合,它更是我那段时间思考、挣扎与成长的忠实记录。这些文字,如同树木的年轮,一圈一圈,记录了阳光、雨水、风暴和干旱。它们不是被“生成”出来的,而是从我的生命里“长”出来的。
AI的“写作”则完全不同。它区分了两个关键的词:生成与生长。AI所做的是“生成”。你给它一个主题,一个要求,它通过复杂的算法和庞大的数据库,在极短的时间内计算出一个“最优解”——一篇结构完整、语法正确、逻辑清晰的文章。这个过程是一步到位的,是以结果为导向的,而不是过程本身。你看不到任何生产过程中的痕迹,没有犹豫,没有挣扎,没有废料。
这正是AI写作最令人着迷也最令人不安的地方。它的高效与完美,恰恰抹去了过程的价值。它让我们误以为,表达就是找到那个唯一的、正确的答案。但人类真正的创造,魅力恰恰在于过程本身。一个书法家在宣纸上留下的墨迹,其价值不仅在于那个字本身,更在于运笔时的力度、速度和节奏所构成的独特气韵,甚至一滴偶然的墨点,都可能成为神来之笔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原帖,有着明显删改的痕迹,但后面无数次的重写,却再也写不出“群贤毕至,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”那天的豪迈。
AI生产的是信息,而人类在文字中长出的是血肉。AI的文本是光滑的,而我们的文本布满了粗糙的、可触摸的质感。这些不完美的痕迹,这些修改、涂抹和犹豫,正是我们在时间中摸索前行的知识结构和情感记忆的碰撞,所留下的最宝贵的证据。它们是刻在我们作品里的指纹,宣告着这件作品的独一无二,以及它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。
有温度的内容只有人类可以做
几年前,挚爱的亲人离世。在最初的剧痛和麻木过后,我开始做一件看似毫无意义的事:给他写信。我明知道这些信永远不会被读到,地址栏上只能填上一个虚无的“天堂”。我写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只是日常的琐碎:今天天气很好,楼下的猫又生了一窝小猫,我尝试做了你最爱吃的那道菜,但味道总是不对……
我为什么要写?我不是为了传递信息,更不是为了获得回应。我在写的过程中,其实是在对抗。对抗遗忘,对抗虚无。每写下一个字,都是在确认那些共同的记忆是真实发生过的;每讲述一件小事,都是在拒绝让一个鲜活的生命彻底沦为冰冷的死亡统计数字。这些文字,是我伸向虚空的手,试图抓住一些正在流逝的东西。它们充满了我的思念、我的不舍、我的恐惧,也充满了我的爱。这些文字是有温度的,因为它们浸透了一个有限生命面对永恒失去时的全部情感。
这或许就是写作最终极的意义。在AI可以生成海量完美文本的今天,我们亲手写作的价值,不在于信息的生产效率,而在于它是一种存在性的证明。因为我们是“向死而生”的生物,我们的生命被一个明确的终点所定义,所以我们才会有如此强烈的欲望去记录、去表达、去创造,去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小标记。我们的写作,本质上是一种与自身必将消亡的命运所做的抗争。
一个永生的AI,无法理解这种抗争的悲壮与美丽。对它而言,时间是无限的,信息是可以无限复制和存储的,没有什么是真正会失去的。因此,它的创造没有那种源于有限的紧迫感和珍贵感。它无法理解,为什么人类会对着一张褪色的旧照片流泪,为什么会把一封信读了又读,为什么会用笨拙的笔迹,写下那些明知无人回应的话语。
AI可以模仿我们所有写作的技巧,可以分析并复制所有伟大作家的风格,但它永远无法复制我们写作的那个最根本的动机:因为我们会死,所以我们才要写。我们的文字,是我们短暂、脆弱、却又无比炽热的生命在世间留下的回响。它或许不完美,或许很笨拙,但它带着我们身体的温度,带着我们心跳的节奏,带着我们每一次呼吸的印记。
所以,尽管AI的浪潮奔涌而来,我依然会继续写下去。因为我知道,当我在写作时,我不仅仅是在组合词语,我是在确认我的存在,是在用我有限的生命,去触摸无限的时间。
这份源自肉体、源自恐惧、源自命运的写作,是AI永远无法共情,也永远无法替代的。这是作为人类,我们最温暖的特权。
本文由 @KK的慢变量 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。未经作者许可,禁止转载
题图来自Unsplash,基于CC0协议
- 目前还没评论,等你发挥!


 起点课堂会员权益
起点课堂会员权益